《学术界》(月刊)
总第292期,2022.9
ACADEMICS
No.9 Sep. 2022
北欧合作社运动及其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张德峰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北欧合作社运动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兴起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些北欧雇佣劳动者、小生产者和中低收入消费者等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选择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取得合力以同垄断市场谈判权力的强者相抗衡。同时,北欧合作社一直发展良好,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合作社部门。北欧合作社既通过创造与维持生产性就业创造巨大财富,也平等地分配财富,还通过满足人的各种基本需求提升国民幸福感。北欧合作社运动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有二:一是合作社的功能与共同富裕目标完全契合;二是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城乡各类合作社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斯堪的纳维亚;合作社;团结经济;共同富裕;城乡合作社立法;中间道路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9.020
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和芬兰(有时统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平衡社会的典范,它们不仅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1]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2]与此同时,北欧亦有着举世闻名的强大的合作社部门,“世界各地合作社的组织者、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都熟知斯堪的纳维亚合作社是比较古老、规模较大且运作良好的组织。”[3]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促进建议书》(2002)中指出,“一个平衡的社会必然有强大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存在,也必然有强大的合作社的、互助的和其他社会的与非政府的部门存在。”[4]即,一个平衡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强大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合作社(互助)部门和其他社会(非政府)部门的协同作用。那么,北欧合作社是怎么产生的,发展状况如何?北欧合作社在北欧的财富创造、财富分配以及国民幸福感提升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北欧合作社运动给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对此,本文拟一一予以探讨。
一、北欧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概览
(一)北欧合作社的产生
北欧合作社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挪威第一家合作社商店于19世纪50年代开业,[5]瑞典第一批消费合作社产生于1852年,[6]丹麦第一家合作社商店成立于1866年,[7]冰岛合作社于1902年开始组建合作社联合社,[8]芬兰的合作社运动到1903年已经“牢固确立”。[9]从北欧合作社运动兴起情况来看,北欧合作社产生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当地人的基本需求,“为了理解合作社对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许多活动均始于满足本地需求的倡议。为了调动本地资源,活动的开展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采取合作社、互助组织或协会等自治组织的形式……” [10]
不过,满足当地人基本需求的方式显然可以有很多种,而北欧人为什么选择合作社形式则与这些合作社参与者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相关。2009年,一份提交给“合作发展苏格兰”(CDS)[11]的报告对苏格兰、芬兰、瑞典和瑞士四国合作社部门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人们(包括瑞典人和芬兰人)选择合作社的原因:“为了解释特定合作社部门的兴衰,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家指出合作的动力来自市场失灵。如果初级生产者被隔绝于新兴市场之外,则他们将倾向于组织运输合作社和营销合作社。如果他们被迫依赖于私人贸易商来购买投入品或提供信贷,或他们被迫向处于垄断地位的‘中间商’出售产品,则他们也可能会成立合作社改变这种状况。同样,如果消费者被迫为掺假食品支付高价,以及如果消费者被绑定在其与小型零售商之间基于信用的关系中,则他们再次将希望有机会消灭‘中间商’实现自给自足。在瑞典和芬兰,20世纪20年代农民和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卡特尔,这些卡特尔从化肥到灯泡等一系列产品均向他们收取垄断价格。市场失灵还包括因无人提供某种重要商品而出现了市场缺口,这解释了20世纪初瑞士和芬兰信用合作社为什么会快速增长。”[12]
可见,北欧合作社的参与者是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雇佣劳动者、小生产者和中低收入消费者等个体,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在生产、营销、消费、融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他们希望借助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取得合力以同垄断市场谈判权力的强者相抗衡。最终,这些弱者争取到了公平合理的交易结果,或者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更好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
(二)北欧合作社的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欧合作社已经发展得非常普遍。例如,外来芬兰的“游客尤其对他们在村庄和小城镇的显著位置上遇到的合作社商店印象深刻,对赫尔辛基的埃兰托合作社的宏伟建筑印象深刻,对两家批发商的总部和工厂印象深刻”。[13]美国旅行家阿格尼斯·罗瑟里在1936年这样描述芬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合作者!……整个社会结构都渗透着合作社。”[14]又如,在挪威,合作社银行与保险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意味着,到20世纪30年代末,社员们可以在当地合作社的怀抱中度过大半辈子,这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15]
最早让全世界对北欧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产生深刻印象的,当属1936年美国记者马奎斯· 柴尔兹的Sweden:The Middle Way,The Story of A Constructive Compromis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一书中的介绍。该书详细描述了瑞典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历程,并高度赞扬了瑞典合作社的实用主义,称瑞典合作社“与通往乌托邦的捷径关系不大。人们的兴趣、精力和意愿都集中在面包、胶鞋、住房、汽车轮胎、保险和电力的成本上……这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而非为了利润而生产的制度。”[16]该书认为:瑞典在当时的两个政治极端(美国和苏联)之间实行了有效的妥协——即“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而瑞典能够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解决其社会问题,主要就在于其强大的合作社运动和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管理的结合。[17]该书出版不久便成为畅销书,瑞典合作社随之为全世界知晓,“中间道路”亦由此成为一个国际流行的政治词汇。同时,北欧合作社运动也曾引起了“罗斯福委员会”的注意,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设立以审查欧洲的合作社企业。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对国外的合作社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瑞典。几个月前出版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中间道路》……我对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沿线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他们让这些合作社运动与私营企业和各种分销商一起愉快而成功地存在,两者都赚钱。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值得研究。”[18]
经过近200年的发展,今天的北欧合作社部门愈发强大,这种强大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合作社种类多、业务范围广。在北欧,“尽管合作社多存在于与农村社区和第一部门生产者(农民、渔民、森林所有者)相关的行业中但合作社事实上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大多数主要部门。在传统上,合作社在金融领域也有影响力,其形式包括合作社银行、储蓄银行和互助保险公司……除了传统类型的合作社之外,在社会部门(尤其是瑞典)、能源部门(尤其是丹麦)和文化部门中还有少量新的小型合作社。总的来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社覆盖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从没有或只有几名雇员的非常小的企业到各国的最大企业。”[19]仅以挪威为例,挪威不仅有农业、渔业、消费者和住房四大合作社部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其他合作社还有“商业合作社,如运输合作社和能源供应合作社。此外,在卫生保健和康复、学校、地方广播电视制作、图书馆、洗衣房、冷库、面包房、供水、博物馆、娱乐设施等领域也有较小的合作社组织。”[20]
其二,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大。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相反,北欧合作社的规模总体上较大,“平均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合作社的规模大于其私营企业。”[21]有的合作社甚至规模很大。例如,在芬兰,消费者合作社S Group主导芬兰零售市场45.9%的市场份额(2018年),还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经营Prisma大卖场。[22]又如,在瑞典,由39家消费者合作社组成的瑞典最大的消费者合作社联盟(KF)有社员320多万、净资产373亿瑞典克朗(2012年),KF和消费者合作社共同占据了瑞典杂货零售业21.5%的市场份额(2010年)。[23]再如,Arla Foods是一家由近8000名丹麦和瑞典农民以大致相等的比例联合所有的乳制品合作社,有近1.6万名雇员,是欧洲最大、世界第八大的牛奶和乳制品企业,拥有Lurpak和Anchor黄油等知名品牌,2008年其收入接近500亿丹麦克朗,其中60%来自瑞典和丹麦以外的地区。此外的典型例子还如:Lantmännen,一个由4万多名瑞典农民所有的从事耕作的农业合作社(2006年营业额为48亿美元);Swedish Meats,一个由1.74万名农民(约占瑞典畜牧业农民的四分之三)所有的、拥有15亿美元营业额和4700名雇员的食品加工合作社;SödraSkogsägarna,一个营业额达37亿美元、其社员拥有瑞典南部50%的私有森林的瑞典最大林业合作社,等等。[24]
其三,社员密度大、参与度高。北欧人口中的合作社社员占比非常高,同时,一个人常常是多个不同合作社的社员。瑞典人口1040万,“50%以上的瑞典自立居民是各种合作社的成员。”[25]芬兰人口550万,有“90%的芬兰人是合作社的社员”,[26]同时,“芬兰合作社的社员数比人数还多。平均来看,一个成年人是两个合作社的社员;那些在农村环境中的人,例如农民,很可能是四个合作社的社员。”[27]挪威人口540万,“超过200万挪威人是合作社社员,其中许多人属于几个合作社。”[28]丹麦人口580万,“丹麦人在一个或几个合作社中成为社员是司空见惯的。”[29]
其四,合作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北欧合作社的种类多和业务范围广、规模普遍较大、社员密度大和参与度高等,决定了合作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芬兰,“合作社企业是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芬兰后来被其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维尔塔宁描述为一个基于互惠互利的经济体:‘我们没有洛克菲勒或卡内基,但我们确实有合作社’。”[30]北欧其他国家的合作社经济的地位也大致类似,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合作社在国民经济的总体重要性、行业分布和整体发展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31]
二、北欧合作社部门对北欧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积极影响
(一)北欧合作社“既创造财富又更平等地分配财富”
上文已提及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提交给“合作发展苏格兰”的报告在对苏格兰、芬兰、瑞典和瑞士合作社部门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份报告的主要信息是什么?……与其他形式的企业不同,合作社既能够创造财富,又能更平等地分配财富(co-ops both generate wealth and spread it around more equally)。在一场由短期主义、自私自利和贪婪推动的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衰退中,这肯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32]其中的“合作社”,即包括了北欧合作社。
1.北欧合作社通过创造与维持生产性就业创造巨大财富
就业是财富创造之源,北欧合作社部门正是通过创造与维持大量生产性就业岗位创造巨大财富。如上文提及的乳制品合作社Arla Foods 就有近8000名丹麦与瑞典农民社员和近1.6万名雇员,农业合作社Lantmännen有4万多名瑞典农民社员,食品加工合作社Swedish Meats有1.74万名农民社员和4700名雇员,等等。从合作社部门的整体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例如,据国际合作社联盟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瑞典有合作社1.1919万家,雇员5.2231万,工人社员9.6552万,生产者社员16.035万,三类就业岗位合计31万。[33]在挪威,2003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其农业合作社约有6万名社员和1.5万名雇员,渔业共有1.3万名社员,消费者合作社有1.8万名雇员。[34]即,挪威合作社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数至少有10.6万个。可见,相对于瑞典和挪威的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其合作社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数相当大。
同时,发展新合作社也是北欧应对失业的重要方式,这尤其体现在工人或劳工合作社的成立方面。“除了提供就业机会的现有合作社之外,在一些北欧国家和意大利,合作社运动还建立了新的合作社。这些新的合作社是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的回应。芬兰在1993—1998年间建立了700多个合作社,其中330个是工人合作社。”[35] 2003年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局在介绍芬兰“劳工合作社”的成功实践时也说道: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失业,失业率从20世纪80 年代末的约为3%上升到20%以上,对失业危机的共同反应是新一轮工人合作社的设立,1996年,工人合作社为大约450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到2001年,它们为3300人找到了全职工作,为4400人找到了兼职工作。[36]
北欧合作社部门创造财富的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合作社外部,北欧合作社部门像所有私人部门一样为社会大量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从单个合作社来看,如上文提及的芬兰消费者合作社S Group主导芬兰零售市场45.9% 的市场份额(2018年),瑞典消费者合作社联盟(KF)和消费者合作社共同占据了瑞典杂货零售业21.5%的市场份额(2010年)。从合作社部门整体来看也是如此。如芬兰合作社在几个重要行业中都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2015年农业占79%,林业占31%,银行业占35%,零售业占36%。[37]在瑞典,“农业部门中的大部分(如粮食生产和锯木厂)都由从事生产的农民采取合作社所有制的形式。”[38]同时,“瑞典100家最大的合作社企业共雇用约10万名员工,年营业额达4000亿瑞典克朗。”[39]
另一方面,在合作社内部,北欧合作社亦让无数社员获益(他们取得了所需的服务、享受了优惠、增加了收入、获得了工资和其他报酬)。例如,在采购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社员可以分享合作社从外部批量采购物资、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优惠;在农用物资购买合作社和农产品营销合作社,社员可以从合作社联合购买或联合销售的议价优势中获益;在运输合作社,司机通过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且免交各种费用而获得更多收入;社员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信用合作社和保险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机制,可以集腋成裘,凭借社员间的信用,让社员获得融资和投保的实惠;在工人合作社,社员从合作社获得了工资报酬,等等。由于北欧合作社如上文所述具有种类多样、业务范围广泛以及社员密度大、参与度高等特征,因此社员从北欧合作社部门获益巨大。
2.北欧合作社平等地分配财富
合作社对财富的分配,实质上是指合作社对归属于合作社自身的那一部分“财富”的分配,是合作社内部的分配。平等是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体现在合作社各项制度安排中,如合作社为社员联合所有、合作社由社员民主控制(基本表决规则为“一人一票”)等。在分配方面,合作社也是平等的。合作社的基本分配方式,不是按社员的出资比例分配,而是按照社员惠顾合作社的惠顾量比例分配(行业术语称“按惠顾返还盈余”)。此处的惠顾量比例既可以通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实物量或金额反映,也可以通过社员向合作社提供的劳动量和获得的工资额等反映。当然,合作社也确实需要资本,且同样需要向投资者进行分配才能吸引资本,但由于合作社是“用资本干而非为资本干”(working with capital,not for capital),[40]资本的基本角色就是充当合作社的生产要素,因此,投资者只能按合作社使用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对价获得有限的报酬,而不能像投资者所有制企业的投资者那样不受限制地获得资本报酬(行业术语称“资本报酬有限”)。[41]可见,合作社的分配方式,无论是“按惠顾返还盈余”,还是在“资本报酬有限”下的按资本(生产要素)分配,本质上都属于按贡献分配,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方式,也是一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平等的分配方式。
之所以说北欧合作社的分配同样是一种缩小收入差距的分配,理由是:较之于投资者所有制企业,合作社投资者获得的报酬有限而合作社“惠顾者”(即社员)——他们或者作为消费者从合作社购买商品或服务,或者作为生产者向合作社提供产品,或者作为合作社的工人向合作社提供劳动——则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为合作社的利润主要按“惠顾”贡献分配给社员而非按“出资”贡献分配给投资者。例如,上文提及的乳制品合作社Arla Foods由近80O0名丹麦和瑞典农民以大致相等的比例联合所有,“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民的牛奶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它通过一个两阶段的支付系统来实现这一目的,该支付系统将乳制品加工和营销的利润分配给了农民。”[42]又如,一份有关瑞典工人合作社近40年的实证研究表明:较之于由外部资本家/所有者/投资者管理的企业,工人合作社的平均业绩更好,生产率更高,支付的工资也略高,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条件更满意,“在许多情况下,这类企业有助于减少经济不平等,因为除了工资之外,员工还可以从企业的资本中受益(通常以大幅提高养老金的形式体现)。”[43]
(二)北欧合作社通过满足人的各种基本需求提升国民幸福感
如上文所提及,北欧合作社产生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当地人的基本需求。在北欧,除了有我们常见的满足人的生产、销售、消费、融资以及就业、社会融入、体面或有尊严地劳动等方面需求的各类生产合作社、营销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工人合作社,还有满足人的其他基本需求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1)满足居住需求(包括特殊群体居住需求)的住房合作社。例如,在挪威,“奥斯陆40%的住房是合作社的。”[44]在瑞典,“住房合作社确保房屋的建筑适合老年居民以及有孩子的家庭。”[45](2)满足男女平等与民族平等需求的工人(劳工)合作社。如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芬兰工人合作社43%的社员是妇女,少数民族建立了10个劳工合作社。[46](3)满足环保需求的能源合作社。如丹麦有社区拥有的风力发电合作社、消费者拥有的区域供暖合作社、消费者拥有的电力供应合作社、农民拥有的沼气生产合作社,瑞典有农民拥有的生物质供暖合作社、农民拥有的生物质服务合作社。[47](4)满足人身财产安全保障需求的保险合作社。如在瑞典合作社Folksam投保的瑞典移民就“占瑞典人口的六分之一”。[48](5)满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疾病患者等照护需求的照护合作社。北欧国家发展了很多此类合作社,“鉴于合作社是人的组织,它们会对社区遭遇的社会性挑战作出回应……在瑞典,超过66%的私营日托中心都是合作社……一些北欧国家正在地方一级成立‘新’合作社。这些新合作社中有许多是在社会服务和卫生保健部门创建的。例如,芬兰农村地区建立了新的合作社,提供儿童日托,并向老年人提供保健和社会服务。这是对市政当局此前提供的服务减少的回应。在瑞典,合作社形式的儿童日托中心、学校和养老院等新成立合作社也很常见。”[49显然,大量存在的各类合作社对北欧人各种基本需求的满足,大大提升了北欧人的幸福感。
三、北欧合作社运动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一)启示一:合作社的功能与共同富裕目标完全契合
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部署要求明确体现在中央相关会议中。例如,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又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
而从上文所述北欧合作社部门对北欧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积极影响来看,合作社具有如下突出功能且其与共同富裕目标完全契合:(1)做大“蛋糕”功能。合作社不仅为社会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而且让社员取得了所需服务、享受了优惠、增加了收入、获得了工资和其他报酬。(2)分好“蛋糕”功能。合作社对归属于合作社自身的那一部分“蛋糕”,主要按社员的“惠顾”贡献分配给社员而非按投资者的“出资”贡献分配给投资者,这样,合作社投资者获得的报酬有限而合作社“惠顾者”(即社员)获得的收入则更高。这种分配方式既体现了公平,又兼顾了效率;既通过强调社员参与鼓励了勤劳致富,又通过限制资本报酬缩小了收入差距。(3)“提低、扩中与调高”功能。合作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弱者(社员)联合自强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社做大“蛋糕”的过程,既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弱者)收入即“提低”的过程,也是减少社会低收入群体(弱者)人数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即“扩中”的过程;同时,合作社为社会弱势群体做大“蛋糕”的过程,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联合竞争力提升而市场谈判权力垄断者的竞争力相对衰减的过程,从而也是实现对高收入合理调节的“调高”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4)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富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功能。合作社可以满足人的各种基本需求,既包括生产、销售、消费、融资以及就业、社会融入、体面或有尊严地劳动等方面的需求,又有居住、男女平等与民族平等、环保、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还有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疾病患者等照护需求,从而可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富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实际上,合作社的上述功能不仅为北欧合作社运动所证明,亦有其他的印证。例如,对于合作社的做大“蛋糕”功能,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局的一份报告证实,“合作社作为生产企业(主要是自我雇用者的企业)和为社员提供服务的提供者,在促进就业和扶贫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50]根据201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对156个国家的统计,“全球合作社内的或合作社领域内的就业人数至少达2.794亿,占全球就业人口的9.46%。其中,2720万人在合作社内工作,包括合作社雇员约1600万人和工人社员(worker-members)1110万人。合作社领域内的就业,主要指从事自我雇用的生产者社员(producer-members),人数超过2.522亿,他们绝大多数从事农业。”[51]又如,对于合作社分好“蛋糕”和“提低、扩中与调高”功能,2016年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一项实证研究也表明,基尼系数与合作社部门规模之间显示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合作社部门的每一个指标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一个经济体中的大规模合作社部门会削弱不平等。”[52]再如,在2003年第81届国际合作社联盟国际合作社日暨第9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国际合作社联盟在以《让人们美好生活的梦想成真》为题发表的致辞中指出,“合作社在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这样不仅使个人发展得以实现,而且也在国家层面上对全体人民的富裕做出了贡献。”[53]其中提到的“使个人发展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合作社的提升幸福感与富裕精神生活功能。
(二)启示二: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城乡各类合作社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如上文所述,北欧合作社运动表明合作社功能与共同富裕目标完全契合,因此,我国应当将发展合作社经济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北欧合作社运动亦表明,合作社部门对北欧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积极影响,是建立在北欧合作社部门的强大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合作社部门所起作用(的大小)同合作社部门的规模正相关。这就意味着,我国发展合作社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合作社部门。
显然,我国当前的合作社部门离“强大”还很远。从北欧合作社部门的情况看,一个强大的合作社部门具有合作社种类多和业务范围广、规模普遍较大、社员密度大和参与度高、合作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要等特点。而我国当前的法定合作社类型几乎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其业务范围有限、规模普遍较小且运行总体上不规范(不符合“合作制”)。因此,唯有大力发展城乡各类合作社经济,我国才有可能迎来一个强大的合作社部门。
至于发展城乡合作社经济的基本途径,除了需要通过传播合作社知识和世界各国成功的合作社发展经验让人们了解合作社的真谛,还离不开城乡合作社立法的支持。这是因为:
其一,合作社的设立需要法律依据。诚然,北欧五国中的丹麦迄今都没有制定合作社法,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社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性几乎均仅以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为基础”,[54]即北欧(包括丹麦)人可以基于结社自由根据需要组织设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而我国对合作社实行市场准入制,《民法典》第一百条明确规定,“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这就是说,任何一类合作社均须另行依据其他法律的规定才能取得法人资格。然而,截至目前,我国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之外,再无其他立法为其他类型合作社的设立登记和法人资格取得提供法律依据。同时,2022年3月1日起实施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合作社类型也仅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且明确规定“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由此可见,要全面发展我国城乡合作社经济,就必须通过城乡合作社立法解决各类合作社的设立登记这一前置性问题,为各类合作社取得法人资格提供法律依据。
其二,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法律引导、规范与促进。立法可以引导人们成立合作社。以挪威合作社立法背景为例,当初在论证合作社立法的必要时,“法律委员会指出,合作社一般法的缺位阻碍了新合作社的设立。委员会提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在挪威成立的所有企业中,只有0.4%是合作社(该数字不包括建筑和住房合作社)。委员会认为,这表明合作社形式对人们来说还太陌生、太不打眼、太难懂。”“而且在某些部门还存在有向其他形式的组织转变的趋势。即使是那些小规模的、且是基于利益相关方合作努力的新企业,通常也会选择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原因之一可能是合作社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55]2007年6月29日,《挪威合作社法》得以通过,适用于除建筑和住房合作社以及互助保险协会之外所有类型的合作社,[56]成为北欧第四个制定专门合作社法的国家。对于通过立法规范与促进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99年由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国际合作社联盟等组织和机构作为成员的“合作社促进与发展委员会”(COPAC)指出,“合作社只有当其能够在适当的法律环境下运行时,才能向其社员提供最佳服务,从而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57]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促进建议书》(2002) 中也建议,“政府应该提供一个符合合作社的性质与功能、以第三条所宣布的合作社价值与原则为指引的支持性政策与法律框架”。[58]
作者简介:张德峰,经济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合作社经济与合作社法学研究。
文章原载《学术界》2022年第9期,原文PDF版见《学术界》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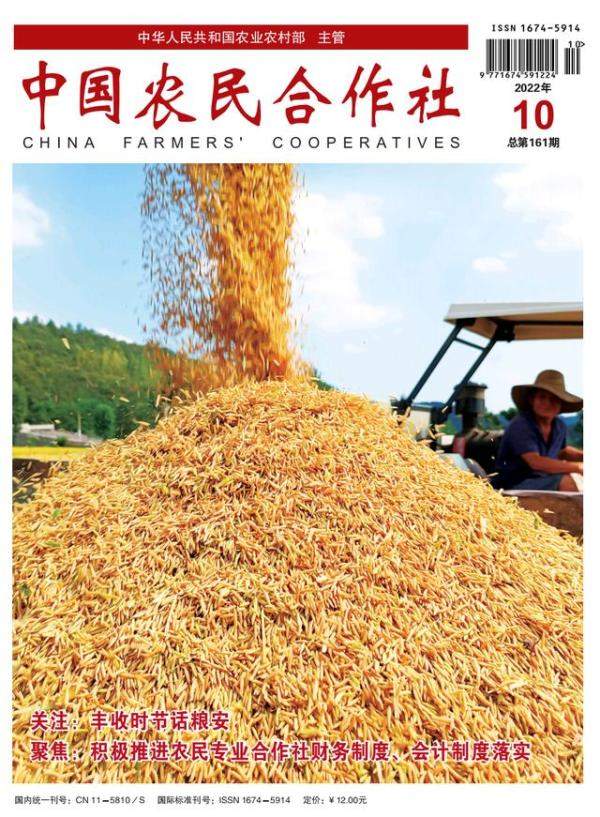
《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