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边缘上探查语言
___
1977年,胡利奥·科塔萨尔访问巴塞罗那。墨西哥《多数》杂志撰稿人豪尔赫·莱维德夫应《多数》委托采访了他。在采访中,作家谈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对拳击和爵士乐的热情以及他的语言。拳击和爵士乐是他的重要创作题材,对他的创作颇有影响。——朱景冬
莱维德夫:如何理解你对拳击的热情?
科塔萨尔:这源自我的青年时代。我从来不喜欢以代表队形式进行的或许多人参加的体育运动。与此相反,我不讨厌观看足球比赛——它激起阿根廷人的热情——,但是它使我感到冷漠。我更喜欢的是个人面对面的运动,如羽毛球赛,拳击。关于著名拳击运动员们的神话在我这样的男孩身上产生的影响——那种热情在童年时代就产生了——肯定也起着很大作用。我一度在路易斯·安赫尔·菲尔波的影响下成长。菲尔波在纽约和登普西争夺世界冠军时我刚满9岁。他的失败是本世纪的悲剧,因为这样的事件在那时使人感到比现在纯朴得多,紧张得多。那时人们没有政治上的忧虑,把他们的爱心、狂热放在别的事情上:电影演员或拳击手身上。我一达到可以去看比赛的年龄,我就经常出入于运动场,观看阿根廷大拳击手们的比赛。从那时起,对拳击的喜爱就保存下来,这在我的作品中反映得相当充分,这个主题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里,在《八面体》中甚至有一篇小说是以蒙松在巴黎的拳击赛为基础的。那一次我去看了,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写了那篇小说。

科塔萨尔
莱:今天有了传播工具,这些工具引导著人们的热情,制造和破坏着神话……
科:很对,这种现象在法国很明显,有一批作家对电视和电台的兴趣比对本身的文学创作还大。使人觉得一本书是通过电视台和电台而存在的,偶然通过期刊存在,但决非凭借作品本身。人们知道,一本书的存在应该是通过评论介绍和阅读。我对群众性的传播工具特别是电视有一种特别敏感的反映。我不属于这个时代。我离开阿根廷到巴黎时身无分文,更没有电视机,所以我老是听唱片或看书,此外也是因为我有这些偏爱。

「爵士乐没有完结,只是发生了变化
就像一棵树,不断长出新枝」
莱:据说,在你听的唱片中,你常选择爵士乐唱片。这是你的另一项爱好。跟拳击一样,爵士乐也死了吗?
科:没有,爵士乐没有完结,只是发生了变化。就像一棵树,不断长出新枝,有的枝条好,有的枝条不好。价值被取代,出现了新倾向。爵士乐包含着巨大的生命力,永远在自我再生,它有群众音乐才有的特点:它的国际性。可以听到好的法国爵士乐,好的墨西哥爵士乐或好的阿根廷爵士乐。别的乐曲却不然。比如探戈,如果抛开它的结构,我们就会知道它是怎样的。应该公平地对待它:从音乐方面说它是贫乏的,几乎不允许个人创造,很难即席创作。要么演奏者必须服从一种曲调,要么听众不喜欢。相反的,爵士乐却是以变奏和即兴创作为基础的。甚至在乐器方面探戈也离不开小提琴、钢琴、吉他和手风琴。当然,对我们阿根廷人来说,探戈保持着亲切的、强有力的价值。在社会学方面,它不仅表现美好的事物,而且表现丑恶的东西(这种情况很多)。我从没有跳过探戈,我觉得人们是从舞蹈开始了解探戈的。总之,我承认,探戈激发了我的爱心;在巴黎我的家里,我有一套珍贵的探戈唱片。当然,天才的胡利奥·德·卡罗的唱片为数不少。

科塔萨尔也能演奏乐器
莱:也许这是一种热情,但更可能是对流亡生活的一种不得已的怀念形式。但是以为流亡的先驱,尽管(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在政治上你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很久之后才开始表现的……
科:我的经历是一个中产阶级、很小的资产阶级和30年代18岁的一代阿根廷人的经历。除了个别情况外,这一代人不参加政治活动。那时的国情是典型的竞选第一主义。在竞选前夕,阿根廷家庭划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在人民大众中,划分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无产者小核心,或无政府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都不是真正参预政治。某位先生只是在轮到他选省长活总统时才想起自己是保守派或激进派。
我从小就为政治的职业化感到惊讶。在某些从事政治的人中间分配公共政治职位。大多数公民都缺乏这种意识和对这种事情的忧虑。所以,我生长在不关心政治的环境中、后来离开了阿根廷,是不足为怪的。一部分原因是不明白庇隆统治意味着什么。我采取了我们这个阶层典型的态度,一种毫无政治意义的反庇隆主义态度。十年后我发现在古巴革命影响下,在阿根廷以特殊的、不完美的形式存在着一个领导强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不理解、只是感觉到旧秩序崩溃了,是使我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但不仅是这个原因。

《春光乍泄》剧照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即景
然而,直到三年前我才认为自己是个流亡者。现在我知道我不能回阿根廷的原因了。1/4个世纪以来,我来去自由。但是我感到讨厌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有点让人头疼的关于我和我的作品的评论中,常常称我是流亡者(我从来不贫道是叫流亡者还是我们阿根廷说的被放逐者)。我赋予“被放逐者”有一种强迫的意味,我认为“流亡”很少是自愿的。被放逐者之所以离开祖国,因为否则的话就杀死他。我的情况不是这样。
奇怪的是,我是从欧洲发现拉丁美洲的,特别是通过古巴革命。因为古巴革命开始时,关于马埃斯特拉的消息、关于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罗宾汉式的人物的消息传来时,欧洲的报刊刊登了。对此,我发生了兴趣,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欧洲,已经年迈了,有可能投身一个我还不清楚的政治觉醒过程。古巴革命胜利时我心想,应该去那里看看。于是我去了古巴。我看到古巴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后想建设一种新生活。根据古巴发生的事情推断,我第一次感觉到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问题。我认为一开始它反映在我个人的态度上,后来我相信它又慢慢表现在我的一些作品里。在我写头几个幻想小说系列的时期,一本像《曼努埃尔之书》这样的作品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对读者,对我自己也是如此。

古巴革命的关键人物卡斯特罗
「我在语言的领域里
在历史的边缘上探察语言」
莱:关于写作问题。在你的创作中,你是怎样触及你曾指出的阿根廷语言中的语义混乱现象的?
科:在我来说,我并没有过多地触及。我出版的作品多是虚构作品、幻想或心理短篇小说。只有几篇作品的内容是所谓政治性的或思想性的。那种语义的混乱现象对我没有影响,因为我不写具体涉及阿根廷形势的作品。我不是人们现在讲的那种政治分析家、评论家、社会学家、政治学者。我是虚构文学的创作者。虚构文学有时深入历史领域,如此而已。
我探察语言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是在我的可能性之内,是从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起,在我这远没有变成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以前开始的。我在语言的领域里,在历史的边缘上探察语言。当然,当你写与当代历史有联系的作品时,那种探察就必须变得特别谨慎: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是加强语义的混乱。如果他的语汇和已经混乱的语汇加在一起,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变得消极了。这在我们拉美各国是司空见惯的。由于缺乏深刻的思想认识,外来的行话就会起作用,并取而代之。我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乘出租汽车,我想我能够这样做。在长长的十分钟里,司机对我说了一通那种行话,一连串的格言和缺乏意义的话,他不加思考,没有连贯的思想。在我最近的两次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现象。

王家卫《春光乍泄》镜头下的阿根廷
莱:你是说,你在写作时很注意简洁明了?
科:是的,表达要明白,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人把简洁明了同思想和表达的贫乏混为一谈,要求知识分子写东西要明白,在简单的意义上的明白,越容易懂越好,让一个冶金工人能够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样利用读物。对明了的这种理解,我一向认为是荒唐的、非常虚假和危险的。有一些作家努力写一部作品,沿着一条路前进,进行某种实验,这种实验把他们置于一种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和必要的水平上——我说的水平,高些、低些无关紧要——一切打算离开这种水平去维护大多数人需要的“简单明了”,其作品几乎总是变成平庸不堪的东西。当一个像詹姆士·乔伊斯那样的作品时,他以自己的水平把从前特别浑浊模糊的事物写得一清二楚。从乔伊斯开始,某些语言的结构澄清了,乔伊斯以某种方式直至不让作品发表,说明了应该怎样使用语言。
「当法国作家贫乏时,法语也是贫乏的
英语亦然」
莱:你提到了博尔赫斯,他在新近的讲话中重复说,西班牙语言是贫乏的。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科:对西班牙作家或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来说,西班牙语是贫乏的,像作家一样贫乏。当法国作家贫乏时,法语也是贫乏的。英语亦然。但是当一位作家叫佛朗西斯科·克维多[1]时,西班牙语就变成了一种极其丰富的语言。我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固定不变的因素,不理解使得博尔赫斯宣布西班牙语贫乏的观点是什么。他有他的理由,因为他对哲学比我懂得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当你在语言需要的水平上驾驭它时,西班牙语是无比丰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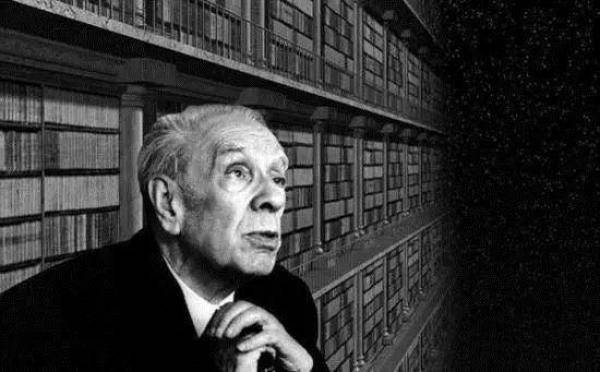
同时代的另一文学大师博尔赫斯
莱:正如有一次博尔赫斯也肯定过的那样,你是为了纯粹的写作而写作吗?
科:最初,我写作是觉得好玩儿。对谈到自己的工作仿佛是一种使命、一种痛苦的牺牲的作家们那种本质上是自负的态度,我一向感到反感。似乎写作是一种分娩,代价极大。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文学就类似性爱,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因为他喜欢,因为他享受了它。当然,其中也有消极的方面。同样,在爱情上也会经受折磨,但是它的结果终归是积极的。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在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某些段落时,我感到非常费力;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我为他们感到痛苦。不能说,写《曼努埃尔之书》的结尾是容易的。

科塔萨尔与其爱猫
作家有权在他认为更愉快更有益或或更有意义的方向上工作。写“曼努埃尔之书”和后来写一本幻想短篇小说一样有价值、合理和合乎逻辑。尽管我清醒地经历着我周围的厉史现实并且在很多时候向它保持着联系、从而写出了《曼努埃尔之书》,但是同样我也作为虚构文学作者很注意各种各样的鼓动或冲动,但是我没有把它们写入作品。一年后我可能有一部长篇小说或两篇短篇小说发表,其风格和《曼努埃尔之书》一致。它们描写的是发生在阿根廷或智利或某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事情。但是也可能是出版一些新的幻想短篇小说。
[1]佛·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朱景冬 译, 选自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
原文载墨西哥《多数》杂志1977年11月号
| 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学者,“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其主要作品有《动物寓言集》、《被占的宅子》、《跳房子》、《万火归一》等。1914年8月26日,胡里奥·科塔萨尔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1918年回到阿根廷,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定居巴黎,1952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曾获得梅第奇奖。1984年2月12日,科塔萨尔因病离世,享年70岁。
#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请提前告知 #
投稿邮箱:yingchuan@enclavelit.com
编辑:南巫
